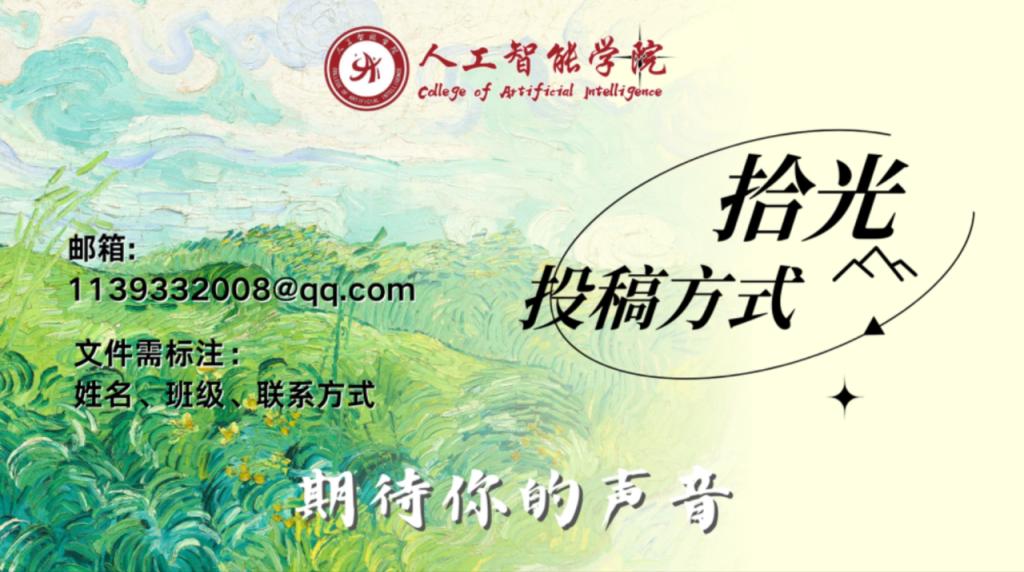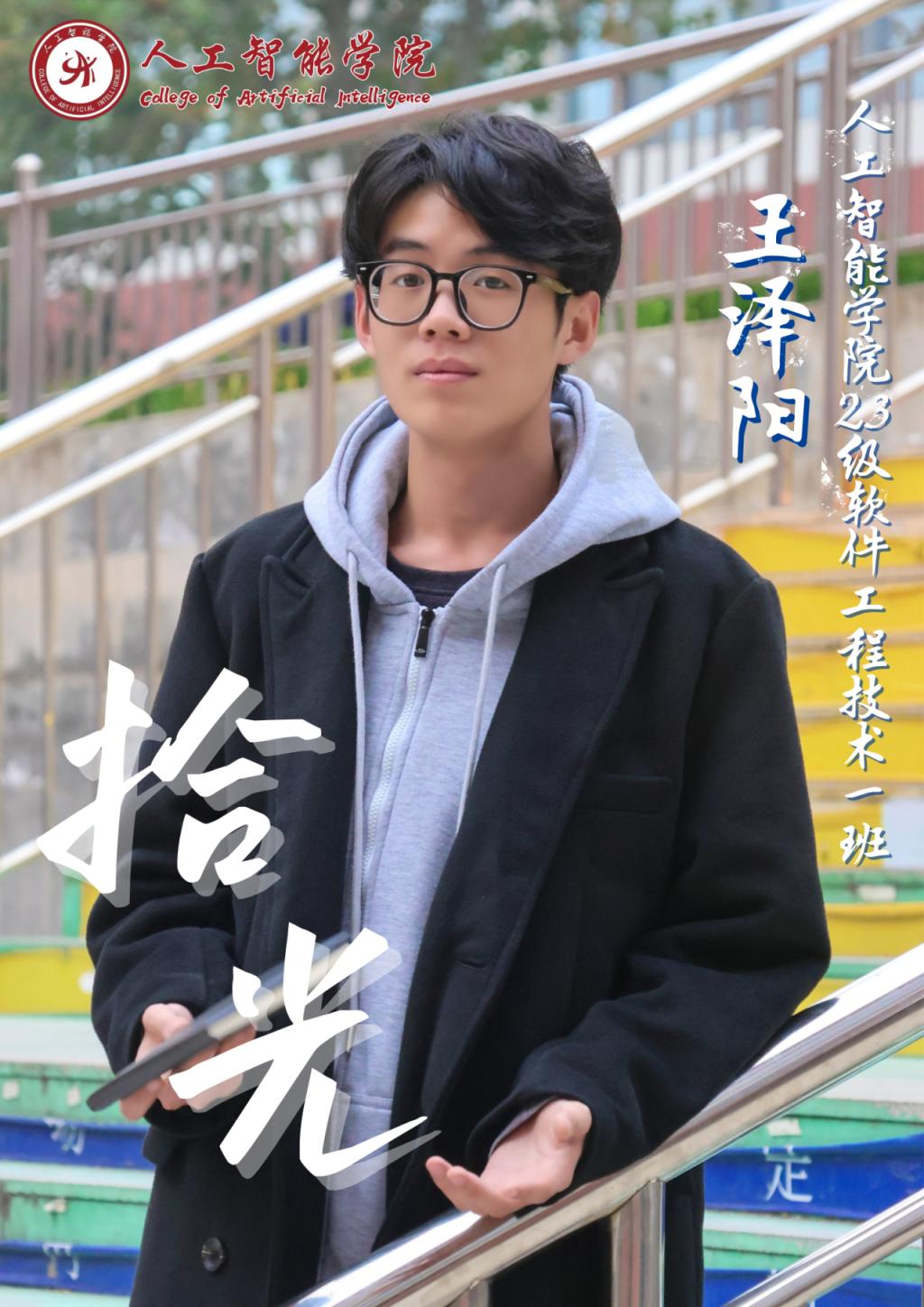

黄昏,一种将时间折叠起来的力量
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,我有幸见证了一场无比壮丽的黄昏。车厢内的光线很暗,过道的右侧是拥挤的三层卧铺。而我就坐在窗帘的侧面,听着《KIss the Rain》轻柔的琴音,望着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疾驰而过。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模糊不清的深暗,只有那轮渐隐的银月依旧纯洁,太阳未落,她却已经悄悄升了上来。
我是一个很喜欢坐车的人,尤其是傍晚或者夜幕。可能是每次出门的时间都比较宽松的缘故吧,我这些年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,坐的最多的便是长途大巴。也正是如此,迄今为止人生中几乎每一场令我遐想的日落,都有着独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车窗。
独自一人出行的习惯让我对旅程慢慢有了新的定义,它的形式不仅仅停留在那目不可及的终点,更不在于耳机里为了缓解过程枯燥,循环了不知道几百遍的歌单。她只是一种简单的缘分,亦可称之为一种力量,在流动静止的时间里窥视着世界上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。

黄昏,是她圣洁华美的嫁衣。
我小学的五年是在村子里读的。因为离家近,加上四里八乡只有这一所小学,每次放学校门口必然挤满了来接孩子的家长。校门的对面是一条还算宽阔的巷道,一般这些家长们都会拥堵在校门两侧的杨柳树边。一出校门,耳边尽是老人们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,小贩悠长的叫卖,偶尔还可以听到几声若有若无得犬吠......
在这样黄昏的陪伴下,我经常高昂着头走在街上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边一轮红日,心想着一定要在余日栖山之前赶回家里。但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我已经走到了家门口,但那黄昏依旧未散,那余日依旧悬挂在山头。除非是在冬天或是秋末,学校放学的时候天色已经蒙黑,也就没了那份急切和热情。
多年以后,当我再次和一个热衷文学的朋友谈起这件事,她很精辟地告诉我,也许那时候的黄昏并不安静,但却是安宁的。我默然,确实如此。
十六岁那年,我来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县城读高中,每次都要坐当天最后一两班的公交车过去。我和父亲就在日落下的车站等车。我父亲是一个话少的人,在等车漫长的一个多小时里他经常一句话也不说。金色淋在他的身上,他拉着我鼓鼓囊囊的双肩包,一直到地平线的尽头渐渐浮现出熟悉的红色警示灯。他才轻轻动了动嘴唇,别老看手机,车来了。我这才抬头,接过他手里的包匆匆上车。
我上车后他并不着急离开,只是点上一支烟,微微抬头。我并不确定他是否是在看我,在狭小的车窗里,我的眼中只有一泻千里的晚霞。他在霞光里伫立,等待公交的轰鸣慢慢远去,手里那只烟还未曾燃尽便被丢在地上。
三年时间里,村前的车站拆了无数次,又建了无数次,唯有那日暮霞光下的背影一直挺立。
若是那夕阳有味道,想必定然是像极了一杯苦涩浓茶,是苦是甜,尽在其中味。
我一直觉得这蕴含希望与孤独,启蒙与荒凉的黄昏是有生命的。无论是在儿时还是中学,亦或是现在,她永远在那方小小的车窗里栖居着。就好像克洛德笔下新古典主义的幻想下,她是一方天穹下席卷而起的浪,不知疲惫地拍打着岸边的峭岩;是灵魂安息的圣堂,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。
在这黄昏下,我可以去拥抱曾经追逐的落日,拥抱霞光下伫立的伟岸,拥抱旅途中每一个夜不能寐的孤独灵魂。最后谱成曲,在某个雨夜的街头用一架老旧的钢琴演奏起来。